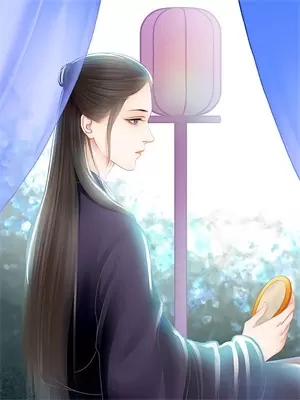我一直以为每个家庭都像我家一样。记忆里,
总有穿着白色狩衣或净色袴的人在我家走来走去。他们摇着铃铛,在榻榻米上贴满符纸,
空气里永远飘着柏木和焚烧艾草的味道。母亲总是跪坐在佛龛前,背挺得笔直,
像一尊快要碎裂的瓷观音。而我的姐姐,夏树,从她能说话起,就能看见“那些东西”。
我记得她五岁时,会指着空荡荡的走廊说:“那个穿着湿淋淋和服的女人在哭。
”也会在盛夏的午后突然蜷缩起来,说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人,他的舌头好长”。
起初父母带她看遍了医生,后来不得不接受事实,转而求助各路阴阳师、僧侣和灵能者。
姐姐因此变得很孤僻。她身上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护身符,书包里,口袋里,
甚至缝在校服的内衬里。她不敢在黄昏后出门,不敢照年代久远的镜子,睡觉时必须开灯。
她的朋友很少,那些东西如影随形,把她变成了一个惊弓之鸟。我则相反。我什么都看不见,
感受不到。我只是活在姐姐惊恐描述的阴影里,活在一个被法事和符咒填满的家里。
我甚至有些嫉妒,觉得那些“东西”分走了父母对姐姐全部的注意力。这种扭曲的平衡,
在姐姐初三那年的梅雨季,被彻底打破了。雨连续下了两周,
家里每一样东西都摸起来湿漉漉、黏糊糊的。霉斑在墙角悄然蔓延,像地图上陌生的国度。
空气里那股柏木和艾草的味道,
压不住一种逐渐浓重起来的、像是腐烂泥土和旧衣箱混合的怪味。姐姐变得越发沉默。她说,
有个“新的”跟着她回来了。她说那不是普通的游灵,它不像其他的只是路过或者展示死状,
它……在看着她。无时无刻,带着一种贪婪的“凝视”。然后,一切开始失控。夜里,
厨房会传来翻找东西的声音,不是小偷,而是某种更笨拙、更急切的声音。
家里的物品会轻微移动位置,杯子放在桌沿,拖鞋头朝里变成头朝外。佛龛前的清水,
会在无人时泛起浑浊的泡沫。请来的阴阳师面色越来越凝重,法事做了一场又一场,
符纸贴了又撕,撕了又贴。但情况没有好转,反而急速恶化。直到那天晚上。
我们被姐姐房间里传来的尖叫惊醒。冲进去时,看到她蜷缩在墙角,
身体以一种非人的角度扭曲着,头向后仰,几乎贴到背脊。她的眼睛向上翻,
只剩下浑浊的眼白,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、像是喉咙被堵住的怪笑。“它进来了。
”她用一种完全陌生的、粗嘎的声音说,嘴角咧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,“这身体,归我了。
”母亲当场晕了过去。父亲脸色铁青,他冲上前,试图按住疯狂挣扎的姐姐。“夏树!
你醒醒!看着我!”父亲吼着,声音里是恐惧也是愤怒。被附身的姐姐力大无穷,
轻易就挣脱了父亲,反手一推,父亲踉跄着撞在书架上。“她”歪着头,
用那双只剩眼白的眼睛盯着父亲,怪笑着说:“打啊?你打啊?打死这个女儿,
我就去找下一个。”下一个。她的目光,似乎扫过了躲在门口、瑟瑟发抖的我。家,
从那一天起,变成了战场。被附身的姐姐——或者说,那个“它”——开始变本加厉地胡闹。
她会把母亲精心插好的花莲瓶摔碎,把榻榻米用剪刀剪烂,
在墙壁上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污秽物涂画扭曲的符号。饭菜里会被撒上香灰,
干净的衣服被扔进院子里的泥水坑。它熟知家里每一个人的弱点,
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母亲:“你心里其实嫌她是个麻烦吧?这个怪胎女儿!
”它嘲笑父亲的事业失败,它甚至对我说:“你其实在偷偷高兴吧?现在没人管你了,
没人要你了。”父亲起初还试图讲道理,请来更多的阴阳师。但每一次法事,
都像是点燃了导火索。它会疯狂地破坏,用姐姐的身体撞墙,
或者发出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,让整个房子都似乎在颤抖。绝望中,父亲的耐心耗尽,
恐惧转化成了暴力。第一次动手,是在它用污言秽语咒骂母亲之后。父亲红着眼,
一巴掌扇在“姐姐”脸上。“滚出去!从我女儿身体里滚出去!”“她”被打得偏过头,
却缓缓转回来,脸上那个诡异的笑容更大更鲜明了。“呵呵……打得好。再来啊?
这身体的疼痛,可是她在感受哦。”父亲僵住了,手臂颤抖着,最终无力地垂下。
但暴力一旦开始,就很难停下。第二次,第三次……父亲开始用藤条,用皮带。他一边打,
一边哭吼:“放开我女儿!放开她!”而“它”总是在笑,
用姐姐的脸露出那种混合着痛苦和狂喜的扭曲表情,享受着这场由它导演的悲剧。有时,
它会故意激怒父亲,有时,它会装作恢复清醒,用姐姐原本的声音哭着求饶:“爸爸,
别打了,好痛……”然后在父亲心软靠近时,猛地吐他一口唾沫,再次变回那副恶灵的面孔。
母亲试图阻拦,只会让场面更混乱。她跪在地上哀求,求丈夫停手,求那个“东西”离开。
家里充斥着父亲的怒吼、母亲的哭泣、 “它”的怪笑,还有藤条抽在肉体上的闷响。
我躲在拉门后面,透过缝隙看着这一切。我看着姐姐的身体布满青紫的伤痕,
看着她原本清秀的脸庞变得肿胀扭曲。我分不清,那伤痕和扭曲,到底是父亲造成的,
还是那个“它”显现的证明。家,不再是家。它是一个被邪恶寄居,被暴力充斥,
被绝望淹没的牢笼。柏木和艾草的味道,
早已被血腥、汗水和一种更深沉的腐朽气味彻底覆盖。而我知道,那个“它”,
不仅仅在姐姐身体里。它弥漫在这个家的每一寸空气里,在每一次挥下的藤条上,
在每一滴无助的眼泪中。它正在以我们的痛苦和疯狂为食,变得越来越强大。这场大战,
没有赢家。只有不断下沉的我们过了许久父亲找来的那位阴阳师,和以往那些都不一样。
他很瘦,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作服,看上去像个普通的管道维修工,
只有腰间悬挂的一个陈旧褪色的布袋,暗示着他不同寻常的身份。他没有带任何华丽的法器,
眼神平静得像一口古井,走进我家这片狼藉的战场时,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
他甚至没怎么看蜷缩在角落、发出非人低吼的姐姐,只是在屋子里慢慢踱步,
目光扫过墙壁、天花板和拉门的阴影处。他的手指偶尔在空中虚划,像是在感受着什么。
“不是一般的‘凭依’,”他终于开口,声音低沉而沙哑,“是‘家秽’。
”父亲紧张地问:“什么是‘家秽’?”“不是跟着你女儿来的,
是这房子本身‘生’出来的。”阴阳师解释,“积年的怨气、家族的负面情绪、地脉的阴滞,
混杂在一起,像污垢一样堆积,年深日久,成了精,有了形体和意识。
它靠吸食这家人的痛苦和恐惧为生。你女儿灵媒体质,心思纯粹,成了它最好的容器。
”他走到姐姐面前,没有念咒,没有摇铃,只是伸出两根手指,轻轻点在她的眉心上。
“回去吧,”他对着附身在姐姐体内的那个“它”说,语气平淡得像在劝一个走错门的孩子,
“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姐姐的身体猛地一僵,随即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她脸上的表情扭曲变幻,时而狰狞狂笑,时而痛苦哭泣,
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怪声和断断续续的、属于她自己的微弱啜泣。那场景诡异得让人头皮发麻。
阴阳师的手指稳稳地按在那里,嘴里开始念诵一种极其低沉、几乎听不清的音节。
那声音不像是在耳边响起,更像是直接震荡在人的骨骼和心脏里。渐渐地,
姐姐的挣扎弱了下去。她脸上的狰狞褪去,只剩下极度的疲惫和苍白。最后,她身体一软,
晕倒在地上,呼吸变得平稳而微弱,像是沉沉地睡去了。母亲扑过去,抱着姐姐失声痛哭。
阴阳师从他那旧布袋里取出一个巴掌大的、黑乎乎像是陶土烧制的瓶子,
瓶口用某种暗红色的东西密封着。他递给父亲,神色凝重。“你们家这块地,是极阴之地,
最容易滋生这类秽物。这次我暂时将它封入这瓶中,但根子不除,迟早还会有别的东西来。
”他叹了口气,“你找个很远的地方,越偏僻越好,挖一个深坑,至少一人深,把它埋进去。
记住,埋好之后,不要回头,直接回家。路上无论听到什么,感觉到什么,都绝不能回应。
”父亲一脸愁云惨雾,接过那个触手冰凉的瓶子,感觉有千斤重。“大师,
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吗?”阴阳师摇摇头:“极阴之地,犹如沼泽,勉强清理表面,
深处依旧污浊。要么举家搬迁,彻底离开此地,要么……就只能时刻警惕,
保持家中人气旺盛,心向光明,或许能稍作抵御。”他看了一眼昏睡的姐姐和哭泣的母亲,
没再说什么,转身离开了。父亲不敢耽搁,当天下午就带着瓶子和铁锹出了门。
他回来时已是深夜,满身尘土,脸色疲惫,但眼神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。“埋好了,
很远,很深。”他对母亲说。家里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宁静。姐姐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醒来,
整个人瘦脱了形,眼神怯怯的,带着劫后余生的茫然。她对被附身期间发生的事情记忆模糊,
只记得一些破碎的、充满恶意和黑暗的片段。她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,更加害怕黑暗和独处。
家里没有人再提起那段时间的疯狂。母亲细心照料着姐姐,父亲也变得沉默寡言,
但不再轻易动怒。一切似乎都在慢慢回到正轨,只是空气里,
似乎总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冰冷的压抑。几天后,我终究没忍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