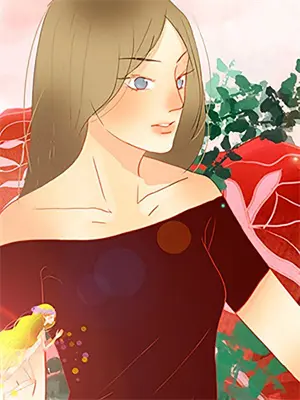
唐同光四年四月一日,夜幕下的洛阳城依旧像往常一样喧嚣。
朱雀大街上灯火通明,胡商牵着骆驼穿梭于熙攘人群,酒肆中飘出烤羊的香气,歌女的婉转唱腔与商贩的叫卖声交织。皇宫内更是灯烛辉煌,将半个夜空映成暧昧的橘红色,那光亮仿佛在燃烧着最后的繁华。
宫墙之外,有老兵驻足仰望,摇头轻叹:“这般灯火,烧的都是民脂民膏啊。”
他的话很快淹没在夜市的笑语声中。
大殿内,酒气与熏香混杂。后唐庄宗李存勖身披一件酒渍斑驳的戏袍,半倚在龙椅之中。他一手提着鎏金酒壶,一手握着空杯,眼神涣散地投向台下。一群彩衣优伶正随着丝竹管弦之声翩跹起舞,水袖翻飞,如梦似幻。
“妙!妙啊!”李存勖忽然摇摇晃晃地站起,踉跄至大殿中央。他举杯指向自己的鼻尖,对着虚空醉语:“李天下,李天下何在?”
这一问,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,殿内歌舞为之一滞。
就在众臣屏息之际,戏班首领敬新磨如一道闪电般疾步上前,众人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脆响——他竟结结实实地扇了当朝天子一记耳光!
时间仿佛凝固。乐师的手指僵在琴弦之上,舞姬的裙摆停止旋动。几位年迈的老臣惊得手中玉杯几乎脱手,面色惨白如纸。
敬新磨却毫无惧色,反而叉腰怒斥:“李天下者,一人而已!尔复谁呼?!成何体统!”
死寂之中,李存勖先是愕然,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:“打得好!打得好啊!赏!重重有赏!敬新磨,朕赏你纹银百两!”
敬新磨并未露喜色,反而躬身沉声道:“陛下,小人适才莽撞了。实是怕皇上过于娇惯我等伶人,误了江山社稷!”
“朕就是喜欢你们,怎会误了江山!哈哈……”朕的江山稳固如山,爱卿,莫忧!"李存勖大手一挥,转身对噤若寒蝉的群臣笑道,“诸卿可知,这天下最懂朕的,竟是这些伶人!你们只道朕爱听戏、唱戏,可知朕为何独独钟情于此?”
群臣面面相觑,无人敢轻易作答。一自诩聪慧的官员起身奉承:“陛下定是觉得戏曲故事动人,曲声悦耳,故而喜爱。”
李存勖闻言,笑声更狂:“故事动人?曲声悦耳?皆是皮相!”他步履蹒跚地踱回龙椅,声音忽然低沉下来,“唯有在这戏中,朕才能忘却自己是皇帝……才能做一回戏中人。”
一直侍立在龙椅旁的宦官李泰适时低声提醒:“陛下,三更天了,明日还要早朝......”
“早朝?”李存勖挥袖打断,醉眼朦胧地再斟一杯,“朕与天下同乐,便是最好的朝政!”
他复又跌撞着走下御阶,一把夺过乐师怀中的琵琶,信手拨动琴弦。曲调初时激昂如万马奔腾,转而婉转似春水潺潺。弹至动情处,他忽然引吭高歌:
“忆昔少年时,金戈铁马疾——
三矢报父仇,朱梁尽披靡——”
这歌声苍凉悲壮,全无平日戏腔的浮华。老将军周德威闻之,不禁以袖拭泪。那些曾随先帝征战沙场的老臣们,个个低头掩面,不忍卒听。
正当歌声绕梁之际,殿外骤然响起凌乱而急促的脚步声。一名浑身浴血的军校踉跄冲入,扑倒在地,嘶声裂肺:
“陛下!汜水关……失守了!叛军已过偃师!”
“哗啦——”李存勖手中的琵琶应声落地,丝弦尽断,余音凄厉。
仿佛呼应一般,殿外远远传来沉闷的战鼓声,如惊雷炸响,震得殿梁上的积尘簌簌而下。
“报——!”
又一名传令兵连滚带爬闯入殿中,声音凄厉欲绝:“陛下!郭从谦率禁军反了!正在猛攻端门!”
方才还沉醉在歌舞升平中的大殿,瞬间乱作一团。杯盘倾倒,官员惊呼,唯有李存勖僵立原地,眼中的迷离醉意骤然消退,迸发出多年未见的锐利寒光。
他一把扯下身上华丽的戏袍,露出内里久未着身的软甲,声音沉静如铁:“取朕的铠甲来!还有,把朕的金弓取来!”
宦官们慌忙抬来沉重的明光铠。李存勖抚摸着冰凉甲片,忽对呆立一旁的敬新磨笑道:“阿磨方才那一巴掌,打醒了朕这个‘李天下’。”
他迅速披挂上阵,系紧胸前束甲丝绦,目光如电扫过瑟瑟发抖的群臣:“诸卿可还记得,朕年少时在晋阳宫受封的故事?”
老将军刘德威颤声应道:“老臣记得……先帝临终时,赐予陛下三支令箭……”
“不错!”李存勖眼中燃起烈焰,“第一支箭,要朕报朱梁之仇;第二支箭,要朕击退契丹;第三支箭,要朕扫平天下!”
他大步走向殿角鎏金木匣,取出一把装饰华丽的宝弓与三支躺在壶中的羽箭。
“朕二十岁继位,第一战便大破夹寨,生擒朱友珪!”他挥舞羽箭,在空中划出寒光,“那时朕亲率五百铁骑,夜渡黄河,直捣敌营……”
殿外喊杀声愈来愈近,火光已将窗纸映得通红。李存勖却恍若未闻,完全沉浸于往事之中。
“柏乡之战,朕以三千步兵大破梁军三万!那一战,朕就是用的这三支羽箭,亲手射杀梁军主帅……”他瞥见铜镜中自己满头珠翠的倒影,声音忽然一涩,“可如今朕拉这张弓,肩胛却疼得很。”
那顶今晨新编的牡丹冠,此刻在摇曳烛光下显得如此破败可笑。
又一名浑身是血的侍卫冲入:“陛下!叛军已破端门,正杀向此处!”
李存勖仰天长笑:“好啊!让他们来!朕倒要看看,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!”
他猛地转身,肃杀之气弥漫周身,对刘德威等老将厉喝:“尔等还记得如何打仗否?”
刘德威铿然跪地:“当然记得!臣等誓死保卫吾皇!”众将随之齐声应和,一行人毅然踏出大殿,奔赴修罗战场。
与此同时,淑妃宫中。
“娘娘!娘娘!”老宦官福全踉跄闯入,袍袖染血,气息紊乱,“郭从谦反了!兴教门已破,禁宫危在旦夕!”
内殿之中,淑妃慕容氏紧紧搂着三岁的幼子李继颜。孩子的脸庞深深埋在她怀中,只传出压抑的呜咽。她脸色惨白如纸,闻讯身形猛地一晃,却强自站稳。
“皇城禁军呢?皇上呢?诸位将军何在?”
“都乱了!各怀异心,无人死战!叛军…叛军眼看就要杀到内宫了!”福全以袖拭泪,颤手指向宫门,“皇后……她……皇后她……”
话音未落,殿外传来急促脚步声与甲胄碰撞之声,一个尖厉的女声穿透长廊,压过远处喧嚣:
“慕容淑妃!开门!是本后!”
殿门被轰然推开,刘皇后身着常服,发髻微乱,眉宇间交织着狠戾、急切与一丝难以掩饰的仓皇,身后紧随数名心腹宦官宫女与持刀侍卫。
“皇后娘娘?”淑妃将孩子护在身后,强作镇定,“如此深夜,甲士闯宫,所为何事?”
刘皇后目光如刃,掠过淑妃,直钉在她身后那小小身影上:“宫变在即,为免龙子凤孙受辱于乱军之手,本宫特来送继暄一程,保全陛下血脉尊严。”
“送他一程?”淑妃如坠冰窟,将孩子死死护在怀中,“娘娘这是何意?!”
“何意?”刘皇后逼近一步,声音冰冷刺骨,“陛下若有不测,诸子之中,唯他年岁最幼,最易为人挟持!他的存在,对谁才是最大的威胁?慕容氏,你难道不懂‘斩草除根’的道理?本宫这是为了大局,为了不让江山再起波澜!”
她手一挥,身后宦官应声端上托盘,盘中一樽酒盏,一段白绫,静默陈列。
“让他选一样吧。体面些。”皇后的话语不带半分情感。
“不——!”淑妃凄厉嘶喊,跪倒在地抱住皇后双腿,“娘娘!继颜才三岁!他什么都不懂!不会威胁任何人!求您看在陛下骨肉份上,饶他一命!妾身可带他远走,永离洛阳,永不回还!”
“离开?”皇后冷笑抽腿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你们能逃往何处?只要他活着,便是祸根!”她的话语被殿外轰然巨响与骤亮的火光打断,宫女尖叫奔逃:“嘉庆殿……嘉庆殿起火了!”
一名内侍连滚带爬入内:“娘娘!申王殿下车驾已备好,在永巷等候,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!那些金宝尚未……”
刘皇后脸色骤变,逃生之念压倒一切。她瞥了眼跪地哀求的淑妃与那瑟瑟发抖的孩童,最后一丝犹豫荡然无存。
“没时间纠缠了!”她猛地抽身,对左右厉喝,“处理干净!别留后患!”
言罢,她决绝转身,在侍卫宦官簇拥下匆匆离去。
殿内,那端盘宦官面露凶光,再次逼近。
“福全!”淑妃猛地转头,望向一直跪伏在地、浑身颤抖的老宦官,眼中是最后的决绝与哀求,“带他走——!快——!”
这一声呼喊,耗尽了她全部的生命。
福全如遭雷击,瞬间明了淑妃心意。他趁那宦官因皇后离去稍一分神之际,猛地起身,如困兽般一头撞开对方!
托盘翻倒,毒酒泼洒,白绫委地。
福全不顾一切地从淑妃身后抄起哭叫的小继暄,用早已备好的粗布迅速包裹,紧紧搂在怀中!
“拦住他!”被撞倒的宦官尖声厉叫。
另一侍卫拔刀砍来,福全侧身闪避,刀锋划破衣袖。淑妃却在此时爆发出最后气力,扑上前死死抱住侍卫双腿,口中鲜血汩汩涌出,目光却死死锁住福全逃离的方向。
“走……啊……!”
福全心如刀绞,肝胆俱裂,却不敢有片刻迟疑。他紧抱怀中微弱哭泣的孩子,沿着狭窄阴暗的杂役通道夺命狂奔。通道之外,车马喧嚣、女子惊呼与嘉庆殿燃烧的爆裂声交织成地狱交响。
他熟稔宫中每处角落,七拐八绕,躲过数波溃逃宫人与零星搜捕,终至一处废弃宫苑墙角,扒开松动砖石,露出一处狗洞。
先将孩子塞出,自己再奋力爬出。身后,喊杀震天,哭嚎遍野,宫殿在烈焰中轰然倒塌。冲天火光将洛阳夜空映照得如同炼狱。
他不敢回头,将小继颜牢牢缚在胸前,混入街上惊惶奔逃的人流,消失在无尽夜色之中。
---
兴教门城楼之上,火光映照着李存勖染血的面容。
"陛下!这里守不住了!"侍卫长李彦卿满脸是血,指着水门方向,"从那里或许还能突围!"
"突围?"李存勖张弓搭箭,一箭射穿正在攀爬云梯的叛军校尉,"朕这一生,何曾做过逃兵!"
他屹立在城楼望台,望着城中四处燃起的烽火,忽然对身旁的刘德威露出一丝恍惚的笑意:"老将军可还记得,当年我们在此门誓师出征的场景?"
刘德威老泪纵横,声音哽咽:"老臣记得......那时陛下刚刚继位,在此门立誓要光复大唐......先帝赐予的三支令箭,陛下一直带在身边......"
李存勖微微颔首,从箭壶中取出三支特制的金箭——箭羽以金丝缠绕,箭镞在火光中泛着冷光。
"第一箭,报父仇!"他张弓如满月,箭如流星,正中城外一个挥舞令旗的叛军将领。
"第二箭,定中原!"第二支箭离弦,带着破空之声,接连穿透两名叛军的胸膛。
就在他搭上第三支箭时,一支流矢破空而来,正中他的面门。
"陛下——!"众将士的惊呼声撕心裂肺。
李存勖伟岸的身躯晃了晃,金弓"当啷"落地。他望着远处燃烧的宫阙,眼中满是不甘:
"朕......十岁习武......二十岁纵横天下......竟至于此......"
鲜血顺着箭矢汩汩涌出,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,缓缓倒在了他曾经誓师出征的城楼上。
"陛......下......"
一声嘶哑得几乎不成调的呢喃,从伶人善友的喉咙深处挤出。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,在冰冷粘稠的血污与尸骸间,用手肘和膝盖,一寸寸朝着那具再也无法回应他的躯体爬行。
这段路,不过十余步,却仿佛一生那般漫长。
他的手指先触到的,是一片尚带余温的血泊——那是某个不知名侍卫流尽的忠诚。善友猛地缩回手,仿佛被烫伤。他不敢抬头,不敢确认那温热的尽头,等待他的是何种冰凉。
爬行。指甲在铺地的金砖上刮擦出"喀啦喀啦"的涩响,混合着血水的滑腻,让他几次险些扑倒。一具俯卧的尸体挡住了去路,他颤抖着,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尚有余温的同袍轻轻推开。触手之处,铠甲冰冷,筋肉已然僵直。他闭上眼,泪水混合着额角淌下的血,砸落在尘土里。
终于,他嗅到了那熟悉的、独属于陛下的龙涎香气,尽管此刻已被浓烈的血腥气蛮横地覆盖。他鼓起此生全部的勇气,抬起头。
看见了。
那张曾睥睨天下、也曾醉眼迷离的脸,此刻凝固着惊愕与无边的不甘。一支狼牙箭矢深深嵌入面门,箭羽犹在微颤。殷红的血,沿着英挺的鼻梁、紧抿的嘴角,蜿蜒而下,在青石板上绽开一朵凄艳的血花。
积蓄的悲痛终于冲垮堤防,化作一声野兽哀嚎般的恸哭。他不再爬行,而是猛地向前一扑,身体重重摔在庄宗的身侧。他伸出手,想去触碰那张脸,指尖却在距离一寸的地方剧烈颤抖,停住。他不敢,怕惊扰了陛下的安眠,又怕证实这触手可及的永诀。
他转而用额头,死死抵住庄宗尚且温热的铠甲边缘,仿佛这样就能传递他卑微的体温,挽留那正飞速消逝的灵魂。呜咽声被压抑在胸腔里,变成断断续续、如同破旧风箱般的抽气。他整个人蜷缩起来,像一只被遗弃的、受伤的幼兽,紧紧依偎着已然冰冷的母体。
周围的喊杀声、宫殿的燃烧声,仿佛都隔了一层厚厚的水幕,变得模糊不清。他的世界,只剩下眼前这张失去生气的脸。
良久,他猛地抬起头,脸上血泪纵横,眼中却燃起一种近乎疯狂的决绝。他颤抖着,再次伸出手,这一次,坚定地、轻轻地,为庄宗合上了那双未能瞑目的眼睛。
"陛下......"他哽咽着,声音低得如同梦呓,"奴才......送您。"
第六章:烈焰别霸王
望着那张染血却依旧英武的面容,善友突然想起什么。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彩墨——那是平日里为自己画脸谱用的。
他颤抖着调墨,以血为水,以泪调和。用浓墨勾画断裂的帝王纹,以青金色点染悲愤的双瞳,最后用朱砂涂抹那苍白的双唇。每一笔都极其轻柔,仿佛生怕惊扰了君王的安眠。
"陛下,您常说自己英武,不输楚霸王......"他的声音哽咽,"这最后一出戏,奴才陪您唱完......"
他将散落一地的乐器——笙、笛、琵琶、羯鼓,一件件小心翼翼地覆盖在庄宗身上,如同进行着某种神圣的仪式。这些,都是陛下最心爱之物。
随后,他举起火把,唱起了庄宗最爱的《霸王别姬》,唱腔凄厉如鬼泣:
"力拔山兮气盖世——时不利兮骓不逝——"
烈焰应声冲天而起,吞噬了乐器,吞噬了遗体,吞噬了那张浓墨重彩的霸王脸。火光跃动在他泪痕未干的脸上,映出一抹诡异的平静。
远远地,几个老臣跪在火光之外,叩首送别。而郭从谦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火焰中的帝王,眼神中没有任何敬畏与怜悯,唯有复仇得偿的快意。
"快!蠢货,把那箱东珠塞进去!"
皇后的寝宫里,刘皇后钗环散乱,往日精致的妆容被汗水和泪水糊花,状若疯癫。
宦官颤声回禀:"娘娘,车驾实在装不下了......"
"装不下?"刘皇后一脚踢开挡路的锦盒,"把那几幅字画扔了!这些死物,能当饭吃吗!"
她忽然想起什么,冲到梳妆台前,将满满一匣首饰胡乱倒入包袱,珍珠翡翠相互碰撞,发出清脆的声响:"这些都是钱啊!到了河东,还要靠这些打点......"
"娘娘,申王殿下已经催了三次了,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!"
"催命吗?让他等着!"刘皇后一脚踢开一个挡路的玉如意,"本宫这些家当,比他那条命值钱多了!"
马车终于摇摇晃晃冲出宫门,立刻被溃散的士兵冲散。
"是皇后的车!里面全是宝贝!"不知谁喊了一嗓子,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瞬间聚焦。
"抢啊!"兵痞们一拥而上,疯狂拉扯车上包袱。绫罗绸缎、金银器皿散落一地,在火光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
"反了!都反了!这是本宫的金宝!你们这些杀才!"刘皇后尖叫着死死抱住一个紫檀木匣。
一个粗野军汉一把夺过,匣子落地摔开,璀璨的东珠滚落一地,引发更疯狂的抢夺。刘皇后被人群推倒在地,凤冠歪斜,锦袍污损,昔日母仪天下的威仪荡然无存。
"可惜我这一身蜀锦啊,你们这些活阎王,天杀的啊......"她的哭骂声突然戛然而止。
一只破碎的金碗咕咚咚地滚到她脚下——那是她平日用膳时最喜欢的碗。此刻在火光的映射下,金碗上的龙凤纹路依然清晰,却已是裂痕遍布,如同这个即将倾覆的王朝。
申王李存渥好不容易挤过来,一把将她拽起:"姐姐!命要紧!快上马!"
刘皇后被强行拖上马背,仍不舍地回头望着那只金碗,痛心疾首的哭声与咒骂声在夜风中飘散。
这一行人,终究如同丧家之犬,没入了无边的黑暗。
宫阙倾覆,戏,散了场。
但在洛阳城某个不起眼的角落,老宦官福全紧紧抱着怀中的幼子,消失在了黎明的薄雾中。新的故事,总在最深沉的夜色里,悄然埋下种子。
---











